李庆锁双脚带着脚镣,出新城北门,跑到路过村,找到一户人家,只有一个老太太。老太太看到来人满脸络腮胡子,衣服破破烂烂,脚下还趟着脚镣,哗啦啦响着,煞是吓人。李庆锁说:“大娘,你不要害怕。我是从牢里跑出来的,想借你把斧头,砸开脚镣,好回家。”
去了脚镣,浑身轻松。他给大娘磕了个头,说:“你是我的救命恩人,我就认你做干娘了。日后我发达了一定接你去享福!”李庆锁站起身来,却又焦躁不安:去哪儿呢?家,没有了;父母妻儿没有了。忽然想起,旧城的饼子泽人很义气,先到他那里躲躲。于是,他也顾不上看路边的风景,一路奔到旧城,来找饼子泽。
旧城是个大集,每逢双日,方圆百里的人们,推车的、挑担的、骑驴的、走马的都来“赶集”,有些赶大车载重货的,都是头一天来到这里。集市上,摩肩接踵,人头攒动,项背相望,游人如织,车水马龙,熙来攘往,填街塞巷,好不热闹!
“你们刘老板呢!”一个风尘仆仆,满脸络腮胡子的大汉进了店铺。
小伙计一看,这是何方神圣?活煞煞一个猛张飞!连忙向后院一个传呼,一个柔软却底气十足的声音道:“哪位朋友来了?”话音未落,一个精瘦麻利的小伙来到门厅。“哦,李兄驾到啊,失迎失迎!”
李庆锁说:“饥死我了,快给我弄点吃的。”
饼子泽说:“理应给老兄接风,我这小铺可不行,今天咱去吃大馆子。”
二人出门往西走了时间不长,来到西大街路南旧城非常有名的魏春饭庄,跑堂的清脆一声喊:“贵客到,二楼雅间请!”
二人刚一落座,小伙计一手提着茶壶一手扣着小碗,手腕一抖,两只茶碗滑到客人面前。
李庆锁说:“感谢老兄两次去监狱看我,还给我带去那么多好吃的饼子,还有那焦黄够劲的山东大烟叶。”
饼子泽说:“我应该感谢你,什么事都自己抗住了,要不然我也就进去了。”
李庆锁说:“自己兄弟,什么也不说了,今天咱俩就结拜为兄弟。”
饼子泽说:“正合我意!”
俩人双拳紧纂,跪拜在当地:苍天在上,我兄弟二人在下,今天兄弟二人结拜,以后有福同享,有难同当,同攀高山,共闯火海。
俩人各端起一碗衡水老白干,一饮而尽。
这时候,一个人闯了进来。他和李庆锁不认识,就想缩回身子。饼子泽赶紧拉住他:“没外人,并肩子(即朋友的黑话)——李庆锁老兄。”又对李庆锁道:“自己人,踩盘子(黑话即指事先探风)去来。”来人听到这里,也就坐了下来。饼子泽问:“居米(黑话银子)找到没有?”
“有。山根蔓(黑话石)村倒是有一个,这家只有糕(黑话老人)没有芽儿(黑话小伙子),芽儿在汉口开糟房呢。就是‘房瓦’(黑话指正堂)高点儿不好蹬上去。”
“那怕什么!”饼子泽回道,“正好,李兄也分一汤钵子(黑话大碗)。”
他们定好暗线(黑话即指半夜纠伙行动)上托(黑话即掩护作案的“眼线”或“望风人”)。时间一到,饼子泽右手向里轮着三个爪的扒钩,一松手,扒钩飞到房顶的垛口上。饼子泽嗖嗖嗖几下就到了房顶上,他蹑手蹑脚下的房来,打开大门,几个人围住各个门口。饼子泽和李庆锁把住正屋大门,用匕首划开门栓,来到炕前,点着亮子(黑话灯)。老头老太太睁眼一看吓了一跳,哆嗦成一个蛋。李庆锁操着外地口音,说:“我们过不下去了,来你这里借几个钱花花。”“没有!”老头嘴还挺硬。李庆锁拿着匕首在他眼上晃了晃,说:“没有钱也行,那是借你的左胳膊呢还是右胳膊呢?!再不,眼珠子也够我喝3两酒!”老太太赶紧说:“我们也没有多少钱,望你们行行好!”“少啰嗦!谁不知道你家有良田百顷,儿子做着大买卖!少了两千现大洋过不去!”老头、老太太轮番恳求少些再少些。李庆锁吼道:“再啰嗦我们就开搜,搜出多少算多少!”
老头见状,忙不迭地说:“一千一千!就达一下我们!”饼子泽、李庆锁交换了一下眼神儿,说:“看你们老头老太太也不容易,就依你了,一千就一千。”
收了银子, 饼子泽吹了一声口哨,大声说:“弟兄们,收家伙,扯呼(黑话即指离开)。”
天未明,他们已回到旧城。李庆锁看到饼子泽如此不费吹灰之力,就有了如此丰厚的回报,他说:“我那个‘三不管’(三县交界)的地方,兔子都不拉粪蛋蛋的,哪有你们这里这样的‘肥猪’?!哥不走了,就跟你们干!”刘玉泽忙说:“你是哥,在这儿也行,以后咱得报你的号!我永远是你的弟弟,做你的副手!”
就这样,李庆锁在饼子泽处住了下来。

 相关文章
相关文章








 精彩导读
精彩导读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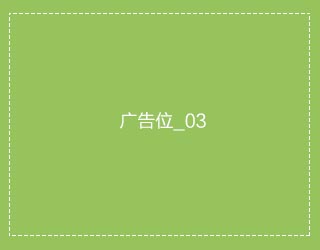
 热门资讯
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
关注我们
